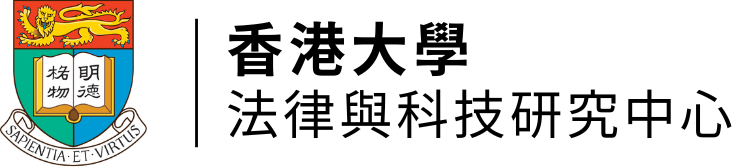2. 被告的提證責任、法律舉證責任及顛倒舉證責任
作為一般原則,被告不必證明自己無罪。不過,該原則存在某些例外情況,例如當被告試圖依據免責辯護或免責例外,或需要推翻法定推定(如果控方能證明其他相關事項,則某些事實可能會被推定為真實的情況)。
被告的辯護理由可能來自控方證人(例如,透過盤問證人和詢問證人),也可能來自被告本人或其他來源。
被告的提證責任
當被告想要依賴一般辯護時,他需要承擔提證責任(減責神志失常和精神錯亂除外,這兩種情況需要承擔更高的法律舉證責任(見下文))。脅迫、自衛、激怒和神智不清等辯護理由必須先由辯方提出,但控方始終要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證明其案件,這涉及到否定被告所提出的辯護理由。
作為一般原則,提證責任的標準是「可能會讓陪審團產生合理懷疑」。如果事實審裁者認為辯護理由可能屬實,則被告有權被判無罪釋放。即使事實審裁者不肯定地相信被告(或者即使事實審裁者在權衡利弊之後更傾向於相信控方證人的說法),辯方證據仍有可能引起對被告是否有罪的合理懷疑。
在被告履行此提證責任之後,控方將開始履行其法律舉證責任。除了證明犯罪的核心要素之外,控方還必須進一步反駁辯護理由。
被告的法律舉證責任
一旦要求被告承擔法律舉證責任,他就必須以「相對可能性的衡量」證明——即他的說法更有可能是真實的。以下是要求被告承擔法律舉證責任的例外情況。
1. 精神錯亂
在被告以精神錯亂為抗辯理由的案件中,法律舉證責任在於被告。在特殊情況下,如果有證據符合標準,法官可自行向陪審團提出此問題。相反,如果控方提出被告的精神狀況問題,則舉證責任在控方,需說服陪審團達到無合理疑點的刑事標準。
2. 減責神志失常
《殺人罪行條例》(第 339 章)第 3 條為謀殺罪提供了減責神志失常的局部免責辯護。簡而言之,辯方必須在相對可能性的衡量下證明: (i) 被告在殺人時神志失常,以及 (ii) 該神志失常嚴重影響被告在殺人時的精神責任。若證據經相對可能性的衡量對辯方有利,辯方的法律舉證責任即告解除。控方應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反駁該辯護理由的存在。
3. 明確的法定條文
一般原則是,如果存在法定免責辯護,而被告選擇依據該免責辯護,則被告必須負責證明該免責辯護。每當控方尋求依據此法律舉證責任的例外情況時,法庭必須依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第 94A 條解釋提出指控所依據的法定條文。
顛倒舉證責任
舉證責任的逆轉意味著被告被要求證明與罪行相關的任何事項或事實。其出發點是有一些客觀的政策理由。例如,《危險藥物條例》(第 134 章)第 47(1)(a) 條規定,任何人如被證實實質管有任何容載或支承危險藥物的物件,則在相反證據證明成立之前,須被推定為管有該危險藥物,並會被推定為知悉藥物的危險性質。因此,控方必須同時證明犯罪行為(actus reus,即罪行的實施或不作為)和犯罪意圖(mens rea,即違法心態)的一般推定被推翻,因為犯罪意圖是根據犯罪行為得到證明的基礎上推定的。這是由於老練的毒品走私者、經銷商和運送者通常會將毒品藏在某些容器中,讓擁有容器的人可以聲稱毫不知道容器中的內容。此類抗辯很常見,對警方和檢控機關而言是一個真正的挑戰。
根據 Hin Lin Lee v HKSAR 和 Kulemesin v HKSAR 的裁決,法庭在施加顛倒舉證責任之前,將考慮四個重要因素:
1. 法定條文用語:除非法定措辭明確說明或以必要含意說明成文法的效力是有意將舉證責任倒置給被告,否則控方必須承擔舉證責任。
2. 法定條文所定之罪行性質:就刑罰及社會責任而言,罪行越嚴重,被告的犯罪意圖之推定越不可能被撤銷,即控方必須證明被告對其罪行之每項要素均知情、有意圖或罔顧後果。
3. 政策考量:法庭必須首先考慮,如果要求控方證明被告的犯罪意圖,則該條文的法定目的是否仍可滿意地達成。
舉例來說,為了鼓勵社會譴責特定行為,當一名男子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時,必須承擔嚴格法律責任,無論被告是否知悉少女的法定年齡或少女是否同意。刑法的威懾效果不僅限於阻止人們參與已知的非法活動,它還鼓勵個人採取預防措施,以避免潛在的非法行為。在此情況下,謹慎避免潛在的非法行為將顯著增強條文對年輕女孩的保護。
此外,法庭對於企業實體在公共安全問題上逃避責任的情況持謹慎態度。例如,為了妥善維護纜車的公共安全,個人在觸犯刑事罪行時缺乏犯罪意圖並非相關考量。否則,若業主聲稱纜車的維修責任在獨立承包商,因此不應負上責任,則可輕易迴避確保公眾安全的立法意圖。
4. 憲法性和人權考量:法庭必須確保顛倒舉證責任與追求合法目的有合理關聯,且實現該目的所需的程度不得超過必要。如果符合這些驗證標準,法庭還必須在整體上信納採用顛倒舉證責任在促進社會利益和對受憲法保護的無罪推定的侵蝕之間取得了合理平衡。
如果在詮釋法例時,有關被告犯罪意圖的推定被推翻,在香港法律下便會出現三種可能的替代方案,即立法原意是否:
- 允許被告在相對可能性的衡量下,證明其作出違法行為時,是誠實而合理地相信有關情況若屬實他並不會干犯該罪行,以此作為免責辯護;或
- 限制被告在其犯罪意圖方面可用的辯護,僅限於該罪名明確提供的法定免責辯護;或
- 使該罪行成為絕對法律責任罪行,因此,如果被告被證明實施或促成了犯罪行為,則不論其精神狀態如何,控方均可勝訴。